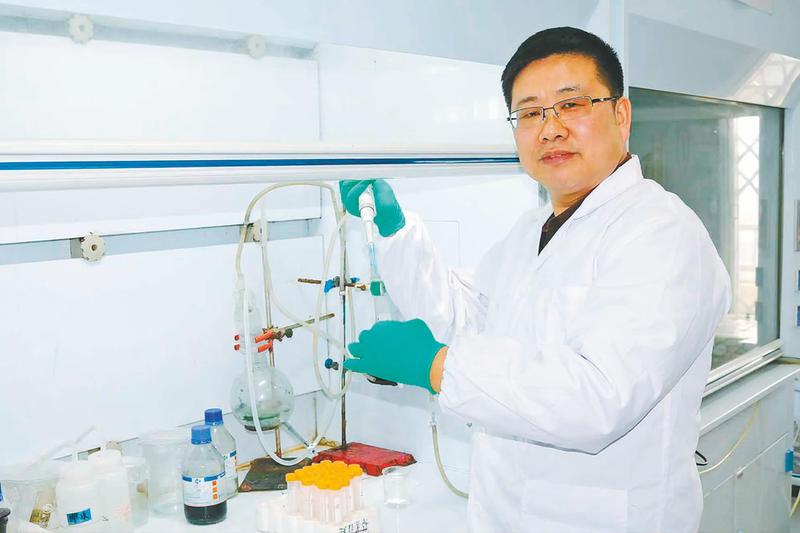
李超教授。受访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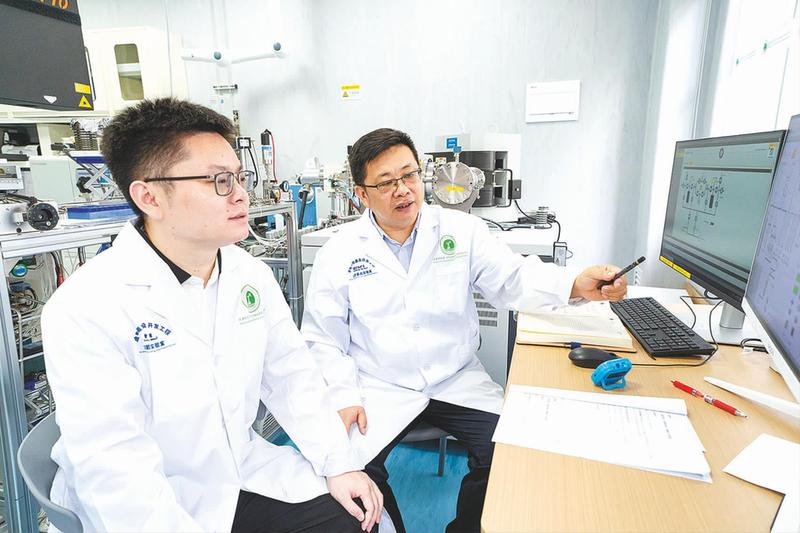 李超(右)正在指导王海洋(左)。受访者供图
李超(右)正在指导王海洋(左)。受访者供图
近日,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李超团队关于地球大气氧含量演化的研究成果发布于Nature(《自然》)。文章从投稿到被接收,仅用了半年时间。审稿人评价该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大气氧含量演化的最佳指标记录。”“为当前大气氧化历史的认识树立了‘新标杆’。”
研究首次以直接、连续的地质证据,揭示地球从无氧环境演进为如今富氧状态历时20亿年,且关键转折点发生在4.1亿年前,并创新性地提出:在短时间尺度上,大气与海洋的氧含量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团队搜罗了上千块跨越数亿年历史的古老岩石,从中“抽丝剥茧”,追踪到有效线索,从而推出演化过程。
树立“新标杆”的过程并非坦途,起初颠覆性的设想还曾饱受争议。李超感慨,成果的取得源于厚积薄发,依赖审慎的求证,以及求真的敏锐与挑战的勇气。
直面挑战
旁人或许只关注研究迅速登上顶刊的光环,但只有当事人清楚,其背后是整整7年的坚持和求索。
采访中,团队成员、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研究员王海洋谈到了2018年的那个秋天。
当时,他正准备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联合培养学习。李超鼓励他借此次出国的机会“跳出舒适圈”,找到一个更具突破性的研究方向,做一些“能有真正价值的工作”。
经过讨论,他们的方向最终落在了地球科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上:地球大气氧含量的升起与演化。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并逐渐达到现今占大气21%的水平?这一重大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李超认为,破解这道难题,不仅关乎对过去的认知,更直接影响人类对当前地球环境变化的理解。
以往对此的研究方法大多依赖于间接指标。科学家通过分析海洋沉积岩来反推地质历史时期海洋的氧化状态,进而间接推测大气氧水平。但这类记录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地球化学改造,像一部被反复誊抄的古籍,难免丢失了很多原始信息,难以追溯。
李超不禁思考,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更直接、更定量的方法,重建远古时期的大气氧含量?是否可以捕捉到来自大气本身且被地质载体直接记录下来的信号?
一项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鲍惠铭(现任职于南京大学)团队开展的研究,为追溯远古大气“配方”带来启示。鲍慧铭团队通过提取、测量并计算石膏、重晶石等矿物中硫酸盐的氧-17负异常强度,来反演地质历史时期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该方法是否也可以来反演古大气氧含量?”李超提出了这个设想。他意识到,这种信号有望成为揭示古大气氧含量的直接指标。
李超当即决定,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联系,希望王海洋能到鲍惠铭的实验室,系统学习并进行硫酸盐氧-17同位素的分析。
不被看好的研究
前人认为,大气氧分子中独特的氧-17负异常信号,能够通过氧化陆地上的黄铁矿,转化为硫酸盐,并随河流进入海洋。然而,这些硫酸盐汇入浩瀚大海,在与海水中的氧原子发生交换时,其携带的氧-17负异常信号很快就会被彻底“抹掉”。
但李超坚信,在漫长的地质时间尺度上,广阔的古海洋中,总会有一些地点在持续地、有效地“录制”着当时的大气信息。
仅有大胆假设还不够。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实验室里,王海洋开启了“小心求证”之路。
王海洋从岩石中弥散状重晶石入手。重晶石是硫酸根离子构成的矿物,前人利用它已在研究古代硫循环和海洋化学方面取得成果,摸索出了成熟、可靠的实验方法。
可实验结果并不如意。王海洋和李超意识到,弥散状重晶石的成因环境复杂,未必能够记录到大气氧的这些特殊信号。
于是,王海洋的研究对象转向了李超提出的沉积碳酸盐晶格“捕获”的硫酸盐,即“碳酸盐结合态硫酸盐”。
实验开展时,恰好碰上新冠疫情暴发,实验室内,单一密闭空间最多允许1至2人戴口罩活动。王海洋硬着头皮打申请,争取到了每天进入实验室的机会。
但重晶石测试已耗费了他半年的时间,结束访问学习的日子眼看进入了倒计时。雪上加霜的是,关键碳酸盐矿物样品短缺。
好在王海洋得到了国内同门的大力帮助。一批采集自华南地区,可满足实验需求的岩石样本从武汉寄出。在全球物流几近停摆的情况下,一个方便面箱大小、装满石头的包裹漂洋过海。
尽管初期测试屡屡受挫,但怀着“至少做完所有的样品”的念头,王海洋坚持了下来。数月后,当关键样品的氧-17同位素数据陆续展示出清晰的氧-17负异常信号,并呈现于电脑屏幕上时,王海洋心中百感交集。
亿年前的氧分子终于“开口说话”。
岁月失语 惟石能言
但这只是一个开端,研究团队需进一步证明这一发现的普遍性。
“大气具有全球性。”李超解释,土壤与地貌会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巨大差异,但大气成分在全球范围内却是基本一致。“既然6亿年前华南的岩石能捕捉到这一氧气信号,那么在同期或不同期,地质背景相似的其他地区的岩石中,理应也能找到类似的记录。”
于是,他们陆续在数年里收集了千余份样品。其中,有的来自中国东南西北各地,有的则借由国际合作,来自澳大利亚、美国与英国同行的储备库。还有部分国内样品是团队成员野外采集的成果。每年6月到8月,正值酷暑之时,他们都会深入山区或无人区考察采样,从破晓直至暮色,往往一待就是一天。
对全球多地跨时代样品的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可信的数据支撑。与多硫同位素等指标进行融合分析后,团队解读了岩石中所记录的直接的大气氧信号,从而首次构建出一个覆盖40亿年的地球氧化史完整框架。
李超介绍,过去,研究者依赖稀有的蒸发岩,只能得到历史上地球大气“配方”几张零星的“快照”,虽然清晰,却无法连贯。而现在,利用广泛分布的碳酸盐岩,研究者首次获得了一套连续、高精度的“地质胶片”,从而有能力绘制出地球氧含量演化的“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团队精准揭示出从24亿年至4.1亿年前,地球表层长达20亿年的过渡性氧化历程。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百万年时间尺度上,大气和海洋的氧含量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就像在粮食有限时,家里老大吃饱,老二就要挨饿。”李超说道,当地球因构造运动导致大量新岩石暴露时,强烈的风化作用会急剧消耗大气中的氧气,并将这些氧汇入大海。所以海洋变得氧化了,但大气中的氧气含量却下降了。
但从数亿年时间尺度上看,老大老二的“生活水平”都在共同提升。那地球是何时成功“脱贫”,步入氧气“小康”社会,让老大老二都“吃饱”的呢?
李超介绍,依据碳酸盐结合态硫酸盐氧-17异常记录,团队首次明确,地球大气氧含量在4.1亿年前持久性地达到现代水平,即攀升至接近21%。富氧环境的形成,也促进了地球复杂生命的繁育。
做有挑战的科学
在破解“大气与海洋氧气此消彼长”这一谜题的过程中,李超团队意外发现,早期地球的海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巨量的溶解有机碳库。这一偶然的发现,或许能为今天在深层、超深层地层中寻找油气资源,提供全新的思路。
“我们也希望借此实现深层油气资源勘查领域从‘0’到‘1’的突破。”李超说,在原始创新上做出突破,将基础研究与国家在能源领域的重大需求真正结合起来,是他一直想走通的路。
1996年,李超踏入了沉积地球化学研究领域。2004年,他赴美从事博士后研究,切身感受过当时国内外在科研条件、整体实力方面的差距。
2011年,李超作为首批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回国发展,也经历了一段“水土不服”的适应期。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8年前后。随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获批,他不仅获得了经费支持,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度:可以更加心无旁骛地挑战那些不确定性极强却意义深远的科学问题。
与此同时,他的团队也逐步步入良性循环。扎实的成果带来新的项目,持续的研究催生新的发现,不断拓展的科学边界又吸引了更多国际合作。
李超感受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国团队的科研角色,悄然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
“和20年前相比,情况倒了个转。”李超感慨道,“就像这次研究,是国际同行把样品送给我们,由我们来主导完成。”
如今,已成为导师的他,格外重视为年轻人“撑一把伞”。他鼓励学生寻找到自己特色的研究方向,成长为各自领域的“参天大树”,而非挤在单一赛道中“内卷”。当被问及科研突破的实现究竟源于何处,李超的答案始终明确:一靠深厚的科学积累,二靠纯粹的科学热爱。
“科学的敏锐,既来自你对一个领域深刻的理解,也来自你内心深处那份热爱。”他说道,“只有两者结合,你才能精准找到那个‘卡脖子’的问题,并拥有一定要解决它的动力。”(杨晨)

